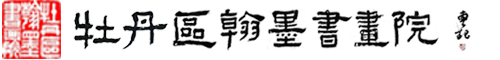【散文】 半生诗酒伴春秋
文/闲云野鹤(山东)
从窗台到案头,诗与酒是我半生未拆的锦囊,裹着岁月的情,浸着日子的香,也藏着没说透的涩与散不去的慌。
十三岁的诗,是窗沿冒尖的嫩芽,沾着桂花落进书桌的痒。语文老师领读“谁知盘中餐”,我在作业本背面画了碗圆米饭,那时能吃碗白米饭是奢望。老师沾着粉笔灰的指尖点过画儿,又弯着腰说:“读诗得懂暖,诗在你妈蒸槐花糕时,灶火熏红的脸上。”后来我总追着她去办公室,看搪瓷杯里茉莉花茶的热气裹着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再把妈妈撒的糖霜、队里分地瓜的抓阄、檐下的虹、雪地里的灰雀,揉进歪扭的字句里。笔记本纸页卷了毛,几页洇着泪迹,写“雪雀”时,想起冻红的手,鼻子一酸就蹭上去了。
年末文艺汇演,我在公社礼堂读自己写的“学大寨”长诗。攥纸的手直抖,念到“地瓜丰收,一年的口粮不再愁。”时嗓子发紧。底下的掌声裹着寒气涌来,村支书在排喊“俺村的娃念得好”。其实哪算诗?不过是把日子串成押韵的句子。可攥着那张皱纸,像攥着灶膛里摸出的热地瓜,甜得指尖发颤,北风刮脸也不觉疼。
大学里的诗,是图书馆台灯熬出的星子,亮得慌,也暗得快。纪宇的《风流歌》贴在公告栏,我抄投稿地址的本子,页脚卷得像干荷叶,每个地址都描了几遍。夜里就着走廊昏黄的灯写稿,写舞厅旋转的裙角、食堂里的啤酒、女同学藏围巾下的浪。十封信有九封石沉大海,退稿信被我压在枕头下,夜里翻身能摸到那纸的凉。直到四块钱稿费寄来,取款单上“XX报社”几个字,被我摸得指腹发红,整夜没合眼。那些熬的夜、咬过的唇、扯过的头发,总算顺着笔尖落进纸页,生了根。
初沾酒是在乡镇包村那年。村头大喇叭读着我写的评论,广播电台连播七天,我总靠在自行车上听完整段。通讯员小李送来登稿的报纸,油墨香混着他裤脚的泥土气,像得了年终奖。头回喝曹州老窖,是在村支书家,黑罐子倒出的酒黄澄澄的,辣得我趴在炕沿直睡。醒来时日落西斜,支书媳妇在灶间喊:“醒了就喝碗粥。”
怕冬天下雪的酒局。乡镇食堂的水杯盛着酒,晃出冷光。副书记拍着我肩说:“包村得走感情,酒场喝得出效率。”村支书攥着我手腕往嘴边送酒,指腹老茧硌得疼:“不喝三杯,征购提留够呛。”酒液烧得食道发疼,我忽然想起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,原以为是送别软意,竟成了乡镇硬滋味,这酒是懂他们的犟。喝到第三杯,我呛出眼泪,老支书却笑了:“这大学生实在,地界儿不揪了。”年底摸到奖状金边,才尝出那酒的余味,是从喉咙暖到心口的热,像灶膛添了柴。
调解宅基地纠纷时,村支书倒了两碗高粱酒,拍着桌子喊“说透理”。管区书记和村民梗着脖子瞪眼睛,我念出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”,老王啐了口:“诗人不知饭菜香!”我端碗喝一大口,辣得吸气:“你承包农场多收了粮,争这垄地有意思?”村民愣了愣,碰了碰李书记的碗:“喝了这杯,俺让他半尺。”
帮老陈承包农场那天,他炖了奶白的鸡汤,从麦囤里摸出瓶纯粮酒:“娃从部队捎的,喝了咱是自家人!”他絮叨着去年玉米减产,我端着杯听,酒在嘴里温温的,忽然想起“隔篱呼取尽余杯”,这酒哪是应酬?是苦日子泡软的人情,连他溅在我手上的唾沫星子,都带着热。
进城到科局,我把乡镇的笔记本塞进行李箱。办公室桌子锃亮,同事穿正装,说话字正腔圆。诗成了抽屉里的月光,亮,却不敢露。午休写“洙水有墨千秋画”,听见走廊脚步声,忙把本子合得严实,指尖攥出了汗。茶水间接水,同事瞥见字笑:“公务员琢磨风花雪月?不如想项目报告。”年轻同事接话:“写诗换不来工资。”我捏着热水杯,手心疼,没敢接话。
半首《大项目观摩有感》的打油诗,改了撕,后压在《政策文件汇编》里;大学样报塞在抽屉深处,纸页发脆,印着当年摸稿费的指痕。可字句总像雨后草芽往外冒:听“项目进度”会想田埂麦穗,见菜市场槐花就念“槐花落进蒸糕香”。只有酒局上敢松口,把对诗句炼成酒令。敬酒时接老领导的话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工资。”慌得心跳,好在老领导笑了;有人叹“评优难”,我端杯喊“天生我材必有用!”酒下肚呛出眼泪,倒应了“闲愁如飞雪,入酒即消融”,不是愁没了,是酒蒙了心,敢说两句真话。
城里的酒裹着规矩的涩。杯子碰得轻,话却要在心里转三圈。高脚杯里的酒能照见人,却没了乡镇玻璃杯的热,少了王维诗里的真心,缺了村支书灌酒的实在。有回喝到半夜,出租车窗映着我松领带、沾酒渍的脸,胃里发空。摸出那页没写完的诗,纸页刮得指尖疼。那几年不碰酒,不是厌了味,是酒里没了诗;少写诗,不是不想写,是办公室的灯太亮,照得人不敢露喜欢。
退休那天,我把样报、残诗、抄地址的本子塞进帆布袋。走出办公楼,风刮在脸上,竟像十三岁大礼堂的话筒,忽然冷静。
退休后的诗,总算敢晒在太阳下。老张看见我贴在阳台的短句,拽着我进诗词协会。工作室墙上挂着田埂、老槐树,他翻我写老年爱情的诗,拍着桌子喊:“把后七夕时代的爱情诗灌醉!”我抖落老笔记本的灰,鼻涕痕、退稿信、残诗都露了出来。重新提笔写秋雨溃秋粮、写古代四大美女、写机场通航高铁通车,写菏泽有了快速高架桥,稿子竟接二连三发表。收到用稿信息时,我趴在阳台笑,老伴端来茶:“嘴都合不上了。”我才知,藏了半生的喜欢早开了花,像阳台的罗汉竹,妥帖,不用躲。
退休后的酒,是和老伙计喝出的酣畅。老吴家客厅的小方桌,摆着盐花生、酱牛肉,本地纯粮酒装在高脚杯里,和乡镇玻璃杯像兄弟。“不为办事,就为聊诗”,他说话时酒洒在桌布上,印个小圈。酒过三巡,我念“酒暖菊香入句来”,他摆手:“‘暖’字硬,得改‘柔’,菊香是软的。”我不服:“秋菊晒了太阳就是暖的!”争得脸红,又笑着满酒,酒洒衣襟也不擦。喝到兴头,他念“诗蘸酒香书快意,酒浇诗兴吐真情”,我俩笑出了声,牙上还沾着肉丝渣。
如今守着阳台,诗与酒成了日子的主角。清晨泡壶茉莉花茶,对着绿植坐半天,灵感来就写两句,笔尖轻响像心尖的喜;写不出就翻老笔记本,看退稿信息,嘴角就弯了。傍晚约老吴来,小方桌摆上,花生配酒,能从诗里的秋雨聊到乡镇酒局。
写《诗酒人生》时,落了句“半盏酒融千种意,一行诗载万般情”。老张凑过来看,眼镜滑到鼻尖:“‘千种意’得有当年的慌,‘万般情’得有藏诗的涩,才舒坦!”说着添酒,酒液溅在稿纸上,晕开的小圈,像十三岁作业本上的圆米饭。
风裹着桂花香进来,夕阳落进酒杯,映着稿纸上洇着酒痕的字,像当年笔记本上的鼻涕痕。这才懂,诗与酒从不是装饰,是岁月陈酒:难时是微光,不让日子冷透;顺时是暖,把柴米油盐、慌与涩,都过成醉人的安。
半生诗酒绕心头,这便是好的年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