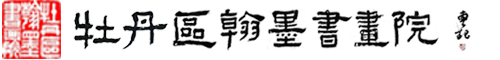开在田埂上的苦菜花
李雪涛/文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鲁西南平原,贫穷就像田埂上的野草,割了一茬又长一茬。父亲在生产队挣的工分,换来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到麦收。每当青黄不接时,母亲总要挎着篮子,悄悄去邻村借粮。
那时,大姐刚上初中,成绩拔尖;我八岁,上小学二年级,是家里的男孩;三妹还在蹒跚学步。二姐十一岁,正读五年级,她书念得也好,作业本上总是一片红勾,像极了田埂上开满的牵牛花。
那个冬天的夜晚特别长。煤油灯在土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,父亲一个劲地抽着旱烟,烟雾缭绕中,娘终于把话挑明:“得有个娃退学!”
在那个年代,按常理该是我这男娃退学--农村看重男丁,我再小也是未来的顶梁柱。可我又哭又闹,死活不肯。父亲的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,后落在正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二姐身上。“二丫头,你……愿不愿退学?”
二姐手中的铅笔停住了。她抬起头,看看爹娘,又看看我们,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一滴眼泪落在作业本上,浸湿了那个鲜红的“优”字。
退学后的二姐,像一株被迫提前成熟的庄稼,在田埂间辛勤劳作。她单薄的肩膀背起沉重的药桶,在麦田的绿浪间穿梭;她弯下尚未长成的腰身,在齐腰的玉米地里除草。秋收时,她掰玉米、摘棉花,指甲缝里嵌满泥土和血丝。待到农闲时节,她又守在昏暗的油灯下学织布,梭子来回穿梭,纤细的手指被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。不到两年,这个曾经握笔写字的小姑娘,已经成了干农活的行家里手。
二姐22岁就嫁了人。回门那天,她穿着大红碎花褂子,带着那个皮肤黝黑、指甲缝里还带着泥土的二姐夫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我那时正上大二,只瞥了一眼就躲回房间。

(网络图片)
过年团聚时,我们聊着大学趣事、单位见闻,笑声不断。二姐坐在角落,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。偶尔她插句话,还是鲁西南黄河岸边老家的土腔:“俺觉摸着……”“恁说这个啥意思?”话音未落,我们就笑作一团。三妹学着她的腔调:“二姐,你这口音可真‘地道’。”二姐的脸一下子红了,搓着手不知该说什么。母亲赶紧打圆场,往她碗里夹菜:“你二姐实诚,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。”等二姐离开后,母亲望着她的背影叹息:“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就是这二丫头,苦了她了......”
对于二姐,我们心里始终藏着说不出口的轻视。这份隔阂,直到父亲中风瘫痪在床,才被现实狠狠击碎。那时我们都不在身边,是二姐二话不说,收拾包袱就搬回了娘家。父亲身子不能动,脾气也变得暴躁,是二姐每天帮他擦身翻身,端屎端尿。长年卧床的病人难伺候,可她从无半句怨言,夜里就支一张小床睡在父亲旁边,一有动静就立刻起身。一年多,四百多个日夜,她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
母亲后来哭着告诉我们,是二姐死活拦着不让告诉我们父亲的病情,说“大姐三妹和弟弟都在外头干正经事,别为父亲的病分心”。我却不以为然:“这年头人心隔肚皮,谁知道她是不是为了那点家产。”母亲气得浑身发抖,一记耳光落在我脸上:“当初该辍学的是你!是你二姐替你吃了这二十年的苦!她学习成绩那么好,要是继续念书,比你们哪个差?”我捂着脸,怔在原地,一句话说不出来。
那天晚上,母亲红着眼圈告诉我,她想把家里那点积蓄分二姐一半,算是补偿。二姐却拒绝了:“我啥也不要,你和爹给了我一条命,把我养大,这份情,我念一辈子,报答不完。”
父亲到底还是走了。丧事办完不久,母亲又被查出了癌症。这一次,留在身边伺候的,依然是二姐。她陪着母亲往返医院、、抓药。夜里母亲疼得睡不着,她就陪着说话,给母亲。直到母亲后合眼,都是二姐守在床头。
今年过年,我们姊妹四个终于在老屋团聚。年夜饭后,大姐捧出一个精致的纸盒,我拿出一个素雅的礼袋,三妹也拎过来一个鞋盒。我们不约而同地将礼物递给二姐——大姐买的是一件质地柔软的暗红色羊毛衫,我选的是一条枣红羊绒围巾,三妹带的是一双深红色牛皮棉鞋。我们都清清楚楚地记得,今年是二姐的本命年。
二姐愣在那里,双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,才小心翼翼地接过礼物。她解开系带,轻轻抚摸着羊毛衫细密的纹路,指尖微微发颤,眼泪无声地滑过她过早爬上皱纹的脸颊:“这太金贵了……在俺们那儿,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……”
我们姊妹三个再也忍不住,紧紧抱住了她。大姐哽咽着说:“二妹,这些年苦了你了……”三妹泣不成声:“二姐,对不起……”我把脸埋在那件熟悉的碎花褂子上,闻到了泥土和阳光的味道,那是二姐身上永远的气息。
泪眼朦胧中,我仿佛看见父母正站在老屋的门槛边,父亲微微颔首,母亲抬手拭泪——他们的脸上,终于露出了久违的、欣慰的笑容。
是啊,就是这个曾经成绩优异的三年级女生,用她稚嫩的肩膀,为我们扛起了整片天空。她像一棵深深扎根在黄土地里的麦子,把所有的养分都给了我们这些离穗的籽粒,自己却在贫瘠中坚守了一生。
二姐是一盏温柔的灯,在我们远行的每一个黑夜,始终在老屋亮着温暖的光。
如今我们终于懂得——是二姐成就了我们,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,都铺着二姐未竟的梦想,我们拥有的每一个明天,都源自她默默牺牲的昨天。而这迟来的拥抱与理解,或许正是对二姐半生付出好的告慰!
今年春天,二姐因积劳成疾突发脑中风,虽经治疗仍落下后遗症,只能勉强生活自理。前段时间给她打电话,她笑着说"没事",可电话那头压抑的抽泣声却像根细针,轻轻挑破了我心底封存多年的愧疚。此刻,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在我心中翻涌,促使我将它付诸笔端,任其潜然纸上。我想让这缕墨香穿过多年沉默的光阴,轻轻落在二姐那双布满厚茧的手上--我想告诉她,那个冬天夜晚放下铅笔的十一岁女孩,我们从未忘记,她藏进抽泣里的半生委屈,我们将用余生的陪伴去慢慢抚平。就像俺鲁西南平原上的苦菜花,它虽苦,却总在春风里重生。我们的二姐,也一定会在我们血浓于水的亲情里,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春天!
作者简介:李雪涛, 男,网名:山东老李。 工作单位:山东省菏泽市鲁西新区岳程街道办事处,山东省菏泽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,喜欢用文学的思维观察社会,洞悉人生,曾在国家省地市级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发表散文、随笔多篇。